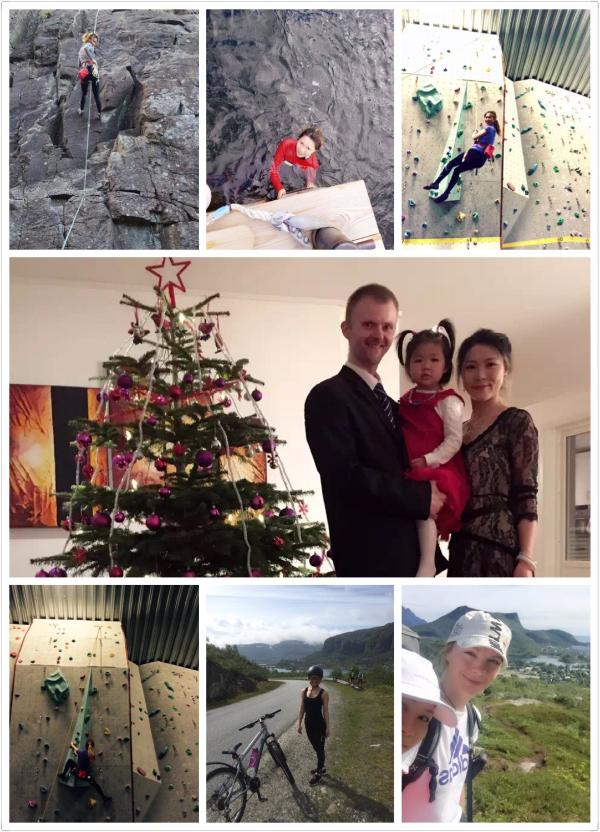发布时间:2024-07-15 访问次数:
落霞、远山、霓虹、庭院,山城黄昏的景致显得更加妩媚、动人。久坐之后的我,每每这样凭栏远眺,顿觉倦意全无、如释重负。此时,依旧立于阳台的我,心中却涌来一阵对草堂的回忆和眷恋,一切都那么鲜活清晰,恍如昨日。
笔下的草堂不在锦官城,也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未曾住过诗圣真身,也未曾有过游客造访。它在离成都府百余华里的毛家院子,一个从未在中国地图上明确标注的地方。然而,无论日思,还是夜梦,它都无数次让我魂牵梦萦(ying),爱之切切。
草堂是外祖父、外祖母白手起家、含辛茹苦大半辈子的地方,是母亲、舅舅、姨妈四姐弟成长启航的地方,也是我和众表兄妹童年、少年最爱去的地方。“去外婆家玩!”,对儿时的我来说,总是一份欣喜、一份幸福、一份如愿以偿,母亲总是以这种承诺或宣告来规约或奖赏我的“表现”。
每次去看望外公、外婆,无论有无父母陪伴,无论有无伴手礼,他们都会乐呵呵地接待我,我也会老远老远一见着他们的影子就大声呼喊“外公、外婆,我来啦!”,飞奔着扑向他们早已张开的怀抱。妈妈四姐弟,只有妈妈嫁给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两个姨妈和舅舅他们家都是吃皇粮的城里人。外公、外婆从不嫌贫爱富,反倒是和姨舅他们三家共同扶携、帮衬我家。每次去外公、外婆家,他们都要给我煮一个鸡蛋,后来条件稍好一些的时候,都一定要让我吃上一顿肉才回家。常听母亲生前说,我一岁多去外婆家断奶的时候,特别吵夜,整整折腾了外婆四十天没睡好觉,差点要了外婆的命。
这话我永远铭记在心,后来我少年时特别主动帮外婆挑水、插秧、除稗、收庄稼、做家务等,参加工作后外婆是第一位我邀请到城里来玩的长辈。记得差不多10岁以前,我是一点都不敢吃肥肉的。后来听母亲说,那都是因为我三岁左右时去外婆家,外公看着我喜欢吃粉蒸肉就一连好几顿地让我吃,吃腻了。
舅舅、舅妈都是老师,住得离我们家很近。每到寒暑假、农忙假、外公外婆的生日等重大日子,我们两家都会邀约一起去探望、帮忙或庆贺。去的时候偶有前后不一,但返回途中总是两家大小一路同行。那时没公交车,近10里的路程全靠步行。印象最深的是,三五岁不到七八岁的我和妹妹、表姐、两个表弟返程时都不想走路,一听到可以坐在父亲、舅舅挑的箩筐里,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往里钻。
舅舅是文人,父亲就主动挑大孩子,负责多挑一个。我们几个小不点坐在箩筐里东张西望,一路上咿咿呀呀、指指点点,时不时还大声欢叫、比赛数数和唱歌等,那兴奋劲不亚于现在的孩子去游乐园。
插秧、打谷、割麦、庆生……,毛家院子总会见到我们两家大小的身影,草堂内外总会充盈着我们两家大小的呐喊声、欢笑声,母亲的大嗓门更让整个院子都知道我们回去了。外公磨刀,爸爸和舅舅杀鸡杀鸭,外婆翻箱倒柜找食材,母亲和舅妈洗菜、切肉、炒菜—大人们各司其职,忙而不乱。我和姐弟们不是相互追逐嬉戏,就是好奇地围观他们忙这忙那,遇上切腊肉或香肠的时候,舅妈和母亲还会递上一两片让我们提前享受美味。外公、外婆门前是一条院子里的乡亲们往来田间地头的必经之路,看到我们的身影都会问候几声,言语和神情中透露出对我们一大家子的羡慕
,偶尔也有邻居在饭点的时候端着饭碗来找我们拉家常。面对这样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大人们一般都会招呼他们一起吃点或送一些到他们碗里。
“草堂出孝子!”母亲四姐弟孝敬外公外婆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一家不闻不理、偷奸耍滑。常听母亲和舅舅说,大姨从读中学时就有顾全整个家庭的担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常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每个周末大姨都会把从星期三开始就刻意省下来的白米干饭积攒在一起从学校带回草堂。正因如此,外公、外婆一家六口顺利渡过了生死考验。后来,大姨、二姨都嫁给了军人,有了体面而有保障的工作,因为他们的主动分担,整个家境明显改善。再后来,舅舅、舅妈也当上了老师,外公、外婆的晚年生活越来越幸福了。我们家在农村,虽然经济上无法给外公、外婆直接回报,但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求医问药、下地劳作,爸妈也是竭尽所能地有所分担。母亲几姐弟从不论长说短,对父母、对姊妹都理解包容,互帮互助。记忆中,这样的家庭氛围着实让毛家院子的乡亲们称羡不已。
记得外公、外婆六十大寿那年,二老所有的邻居、亲人和后人都悉数到场,隆重庆贺。那刚好是改革开放不久后的八十年代,大姨把她新买的卡式录音机带了回来,里面播放着《军港之夜》、《东方之珠》、《乡间小路》等流行歌曲,那音乐、那格调、那气派,让整个毛家院子都有了一种“大姑娘上轿—第一回”的新鲜感。有乡亲们问录音机买成多少钱时,大姨说“四百多点”。这一回答不仅仅惊呆了坐在一旁舍不得离开半步的我,好多人都说“天哪!要卖好几头牛才得行啊!”后来,我常给小伙伴夸耀:“我大姨家有一台录音机,价值四百多元呢!”,翘起的嘴角恍惚是在得意我家的家当似的。
八十年代初,二姨一家从新疆退伍转业回到了县城。第一时间,我们四家一起回到了草堂,让外公、外婆高兴不已。那是我对二姨一家最早的记忆,全家大小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我这个“小四川”既感到陌生,又感到了不起!尤其记忆犹新的是,表哥、表姐刚刚十岁出头,个子就跟大人似的,超过乡下同龄人一大截。无论是身高、衣着,还是谈吐、气质都远远让人相形见绌(chu)。庆幸的是,表哥、表姐,包括表弟,他们三人都没给我鄙夷的目光,也没给我城里人的距离感和傲慢样,很快就和我及其他姐弟们玩游戏、捉迷藏等等。“相识”后的眨眼间,我就成了他们形影不离的“跟班”。二姨父、二姨妈更是慈眉善目,询问我的年龄和学习情况,鼓励我好好学习。
后来,我们四个小家庭的走动就越来越多了,一起以外公、外婆的名义在草堂团聚的时机也多了起来。每一次聚会,虽说没有棋牌娱乐和游山玩水,但也觉得时光匆匆、意犹未尽。看似简单的家长里短,大人们商议着怎么为外公、外婆颐养天年,怎么为兄弟姐妹修房造屋、看病就医等出力出钱,怎么为孩辈营造好的学习氛围,怎么样助力孩辈的升学、就业等等。每一次道别,体弱多病的外公都会拄着拐杖跟上几步,目送我们好远,外婆都会陪着我们走出整个毛家院子的地盘后而偷偷地拭着眼泪。
草堂而今无迹寻,唯留吾心一方尊。纵有万贯居豪墅,不及家和睦天伦。毛家院子、草堂,我乡愁最多的一隅(yu),我不可磨灭的珍忆!
文 谭万文